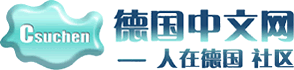|
  
- 积分
- 259115
- 威望
- 99720
- 金钱
- 125
- 阅读权限
- 130
- 性别
- 女
- 在线时间
- 1719 小时

|
37#
 发表于 2005-3-6 12:57
发表于 2005-3-6 12:57
| 只看该作者

31下
那素素抬了头,
尖尖下颌,一瓣初开的茉莉花,清新芳香,犹疑地问她,书好看吗?宝儿。
好好看啊!她夸张的诱惑她,对她比比划划。她是她最好的朋友,年少的友谊纯净芬芳,她觉得好的,必要与朋友一块分享__立刻、马上,待不得明日。
明日还有明日的好,毕竟青春是一场惊喜的盛宴,一天一朵不同的烟花,滴溜溜的升上天空,令她们看的目不暇接,不待散场.
那,你___爸爸在家吗?她问她。
为什么要这样问啊?她边回答边想.不在的吧,一般这个时候爸爸很忙很忙很忙….
那我去.素素欣喜的回答.
为什么?素素,难道我爸爸在家你就不去我家吗?
素素低了头,低声答,宝儿,说实话,我怕你爸爸。
为什么会怕?这素素,爸爸那么那么好,好的无法言说,怎么就让她害怕?简直说瞎话!
她想不明白,她爱他,愿天下所有的人也爱他,看出他的好来,而不是怕.
爱令她盲目,令她看不出他的威严,看不出他的眼里的寒光,那寒光对陌生人徒然一亮的刹那,闪着的是鹫的光___阴沉,俊美,却测探,打量…..
险象环生,步步为营,深至无底的潭水一样!溺进去,必九死一生,永无生天.
素素虽小,但怕的正是那莫名的眼光,混沌而不明朗.乌云压城城欲催.虽说他并不高大.
而她却越发想证明爸爸的好给她,拉了她的手,摇她,去嘛,去我家,我爸爸才不可怕.我爸爸可好可好啦.
俩个人一路蹦蹦跳跳的到了家.
她的书房,整洁宽尚.她随意的拿起一件东西,都那么时尚漂亮,都那么好看可爱,精致适当.且每拿一件,她都不由自主的说一句,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……
我爸爸.
我爸爸.
我爸爸…..
一个于别人是简单的词,于她却是禅___口头的禅,今世的莲花.
___或许正因为她没妈妈,全数的爱,都要在唤爸爸这个词里肯定,那样才能换来人世的自信呀.
说了那么多爸爸.素素垂眉低语笑她,让我好好看会书好吗?宝儿,我知道,你有个好爸爸.
她留她在书房,自己却跑去洗澡.洗着还想着什么,洗完了擦了擦湿滤滤的头发,突然想调皮一下.
素素,她那么怕爸爸,就装爸爸来吓吓她.
于是找来爸爸的衣裳,一件未洗的西装.那么宽,那么大,她套上去,袋中人似的,他的袋中人,却于衣领间闻见一股男人的体香,隐隐的能把人醉了的,令年少的心找不到方向____雪茄,头发,淡淡的古龙香水,三味混杂,那么好闻,且令人闻的有细细的迷茫和感伤…
万般惆怅.
呀,什么时候她长的这么大?
在爸爸的味道里,她悄悄的推开了书房的门,蹑手蹑脚,喉咙里把嗓压,宝儿,你带谁来咱们家?
那素素涑然一惊,回首看来,先看的是她,嫣然笑了,责她,你这个坏家伙,吓我一跳…..
话说了一半却停下,小小的唇半张,目光赶快看到地上,受惊的小兽一样,似遇着强光,无法抵挡.
她也回首,身后,是爸爸!
他也她捉迷藏了.
忙转过身,边喊着爸爸,边扑个满怀于他.他抱住了她,紧紧的搂一下,这是他和她的礼仪.日日,月月,年年,从未变化.
他含笑着问,宝儿,你朋友吗?
她把脸伏他胸上,爸爸,是的,我和你提起过的,她是我最最最好的朋友了…
徐素素!
他未等她出口,就自自然然的叫出她朋友的名字了.
那素素抬起了头,慌张的看他一眼,他的目光谜语般莫测,嘴角却含了笑了,皆是宝儿的面子.
弱小者怯怯的,低声的,叫了声,孙叔叔!
说着因不安,把齐耳的短发撩了一撩,压在半轮月亮后面,那是她处子的耳朵.
这个动作却令他的眼光徒的亮了,亮的耀的怀里的她也觉得光辉灿灿的,从来爸爸只是这样的,看她一个人的,为什么现在看素素也这样了?她突的心里酸酸的,叫了声,爸爸…..也不由的朝那边望去了.
没什么奇特,素素的耳垂上有一颗痣,她早晓得,可爸爸为什么看的痴了?
那不过像一滴流错了地方的暗黑的隐秘的眼泪罢了.
她摇他,五味俱全,至后却都成了一腔酸液,爸爸!
他回过头来看她,刹那,眼里的亮暗了下来,满盘落索,一切空茫.抓不住什么似的,宝儿,你们好好玩吧.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