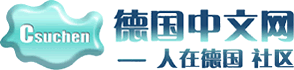|
  
- 积分
- 170192
- 威望
- 46636
- 金钱
- 4
- 阅读权限
- 130
- 在线时间
- 9860 小时

|

杨宽(杨师群老爸)回忆录中的杨师群
第九章支离破碎
原书366页
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
不久,我经过请托,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。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,
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,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“插队落户”,我很不放心,曾多
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。他的母亲去世后,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,再
度请求把他调回,得到了批准。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,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,性格
强横,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。果然,更大的麻烦来了。他回来以后,住在我的雁荡路
寓所,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。据他说,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“插队落户”而家在上海
的女朋友结婚。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,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
具;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,然后由我去付钱,但是他不同意,要我直接把
钱给他。我没有立即同意,他就大吵了起来。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,拜访她的
父母,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,结果他们告诉我“两人只是朋友,目前还没
有到要结婚的程度。”一个星期日,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,他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
,拍着桌子,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。当时,他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,我为此多
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,请求帮助调解,但遭到拒绝。
经过大媳妇和小儿子接连到陈家找我吵闹之后,里弄里议论纷纷,使得陈家处境十
分为难。陈医师只知道哭泣,她的父亲天天劝导她同意结婚,最后为了爱护我,她愿牺
牲自己,就答应了,当了我和她父亲的面说:“如果结婚,仍然一定要保持我的童贞。
”我当着她父亲的面,立刻向她说:“我可以保证,我为了爱护您,我会尊重您的宗教
信仰,保持您的童贞。”三个人一起谈好,她走进卧室去失声大哭了一场。从此以后,
我始终遵守我的诺言。
接着我就向复旦大学方面请求出一张同意我和陈医师结婚的证明,以便向女方户籍地的
结婚登记处申办结婚手续。不料党委书记认为我是知名人物,必须调查清楚女方,才能
给出证明。三个星期后我才得到答复,说经过调查,女方的人很好,这才发给我证明。
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,我到陈家,伴陈医师按照规定,到结婚登记处请求登记结
婚。当时女方单位的同意结婚证明已经拿到。登记处接待的工作人员,认为手续上必须
向我居住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我的情况,当场就打电话联系,放下电话就显出为难
的样子说:“我不能替你们办理结婚登记,据说你的儿子不同意。”我就据理力争:“
结婚是我自己的权利,没有人可以干预。”再经过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考虑之后,终
于给了我们各一份结婚登记证。
婚后,因为我无处安居,就住在陈家,她真心真意地爱护我,随时随地照顾我的生
活和健康,使我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得以痊愈,健康有了好转,从此可以重新开始作学
术研究了。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《战国史》的工作。
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。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(证),
也没有小菜卡。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,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,户
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。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,长期由她使用着;等到大媳妇分
配到新的住处,自己另有小菜卡,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。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,要亲
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,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,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
所认识的;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,我就无法领到了。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
院的医疗证,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,这张医疗证就作废。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,只
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,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,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,
都得请托朋友帮助,很是麻烦。
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
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,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。大
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“工宣队”那里去告我的状,因为我的上司是
“工宣队”。“工宣队”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:“家庭纠纷我们不管。”于是他们更
胆大妄为了,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。
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,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,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,
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,我们夫妇两人、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
在三楼上。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,让她翻到屋顶上,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
,设法拔去铁钉。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“造反”冲击都不敢插手;又因为是星期
日,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,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。到傍晚七时许,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
家交际等候,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,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,想从门缝里塞进来。正当她
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,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,采用了当时造反
派揪人批斗的方式,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,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,一面大声吆
喝,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,拖出大门口,并揿住她的头,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
。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,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、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,
纷纷出来帮助。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,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,让我
的妻子脱逃,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。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
,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,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
的话,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。特别痛心的是,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,竟然指使
小孩也仰起头来,跳着脚,对我不断地大喊:“等我(370页)长大了,替妈妈向你报
仇!”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,当众“勒令”要邻居交出
人来,纠缠不清,一直吵闹到半夜;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我的妻
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,我们才恢复了自由。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
的惊吓,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。
三天后的傍晚,我们夫妇回到家门,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。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
岳父,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,让他出之后再钉,但是小儿子不睬他,仍
然把他钉在里面。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,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
。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。
两次被钉门以后,我为了安全,带着妻子避居到另一位朋友家中。这时小儿子又来第三
次钉门,把我的八十多岁的老岳父单独监禁在三楼上,我只好又去房管处请求派人来处
理。没想到小儿子很快又来第四次钉门。
那时一位邻居看到,出来劝导,向他指出:“你父亲已不住在这里,再这样钉门,
会闹出人命来的。”小儿子不理睬,他想用监禁我老岳父的手段来向我要挟。他预先把
几十支长铁钉截去了钉头,成为两头尖的长铁钉,使得铁钉钉入楼门口和门框而无法再
拔出来。同时他指使几个伙伴轮流在周围巡逻,声称不许拔钉。一位邻居的老太太怕我
的岳父饥饿,买了十个馒头在楼下叫喊,向楼上张望的老岳父示意,叫他用长绳放一只
篮子下来,但是被小儿子的伙伴在巡逻中看到,大声恐吓不准把东西吊上去。这下子邻
居都不敢来救助了。我到处奔走求援,没有一个单位受理,甚至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管。
(371页)经过我十二天的奔走,最后得到市政府里一位领导干部的帮助,才使得公安
局派人来拆除这个被钉死的楼梯门,因为除了整个拆除之外,没有办法拔出铁钉开门了
。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监禁了十二天,十分恐惧和焦虑,当时居民家中都不装电话,我
们无法通话安慰他。他只靠留存的一些米煮薄粥来充饥,度过被禁闭的十二天,从此他
健康大受损害。
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
陈医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仅仅上缴了首饰,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。她只是
为了爱护他人,牺牲自己,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。她伴着我,毫无怨言地
一起承受我儿子、媳妇猛烈“造反”的冲击。当钉门事件发生时,“文革”刚结束,我
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,不少领导干部指出: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,只有向法院起
诉判罪才能解决。陈医师反对这样做,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,以
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,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。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
门事件,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。
婚后我住在陈家,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。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,大儿子,大媳妇和
小儿子常来闹事,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,到苏州、无锡等地去“避难”。当时大
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,仍然不断前来吵闹。大儿子竟然前
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,让他使用,我没有答应。我说:“我和你已脱离父子
关系,不必再来见我。”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,我按当日的承诺,付给小
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,小儿子把扣留的户(372页)口薄归还给我。
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,十分恐惧,不得不沉痛地当场
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。
陈医师于一九八〇年十月,应邀前往美国一所医院担任医师,从此她过着独立的生活,
但仍然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她始终真诚地关心我和鼓励我,安慰着我心灵上的创伤,
无论工作怎样忙,每个星期必定给我一封信,报告她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。当时我
还在陈家,直到八二年春天才搬回雁荡路的寓所居住。两年后我离开上海,飞往美国,
就此又和陈医师住在一起,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她工作之余亲自烹饪各种富于营养而适合
老年人的特殊饮食,对我体贴入微的照顾,使得我身体强健起来,心情愉快,无忧无虑
,生活中充满种种乐趣,让我得以欢度幸福的晚年。
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(373页)家的变故,因为这是“文化大革命
”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急风暴雨
,打破“四旧”和“抄家” 的运动,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,而且冲击到许多家
庭之中,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,代之以残酷无情的“阶级斗争
”。当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,儿子和媳妇们已经
酝酿着“造反”的打算,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,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,就争先恐后地
对我采取 “打”、“砸”、“抢”的造反行动了。他们先是找寻时机,争相夺取我所
有财物和重要图书,接着就大吵大闹,作进一步的要挟,使我无法安居。待我被迫躲避
离去,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,一步步的进逼,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
事件,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。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带来的终极恶果,也是我应该
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。
楊寬(1914年─2005年9月5日),中國歷史學家,生於上海青浦縣白鶴江鎮,蘇州中學
師範科、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,中學時代起即進入先秦學術領域。
1946年任上海市博物館館長,兼任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;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
;1960年轉任參與籌設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, 1970年起專任復旦大學
歷史系教授,生平發表論文兩百三十餘篇,曾參與修訂《辭海》、編繪《中國歷代地圖
集》先秦部份、標點《宋史》等工作。著作有《戰國史》、《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》、
《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》、《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、《西周史》、《中國上
古史導論》等。1984年起與夫人陳荷靜女士客居美國邁阿密,2005年9月5日在美國逝世
,自傳《歷史急流中的動蕩和曲折》出版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