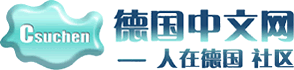杜塞尔多夫的历史文化沉淀!(海涅诞生地和小巴黎来历)
如果不是一次不靠谱的“商务旅行”,我肯定不会主动跑去杜塞尔多夫。
就在不久前,我刚刚见识了所谓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作品。一对夫妇,贝恩德·贝歇(BerndBecher)和希拉·贝歇(HillaBecher),打1960年代起,以对待纪念碑的态度,四处拍摄水塔、风塔、煤矿之类无聊的工业建筑,孜孜不倦,终于集下照片无数,又以回笼调查问卷的精神,依其功能、结构、环境、历史乃至一厢情愿的美学等多重要素,洗牌般排列组合,俨然一幅举世无双的乏味画卷。
这便是我对杜塞尔多夫的第一印象。尽管两口子把照片卖得很贵,尽管他们的确影响了一代德国摄影人,我却很难对影像依附的城市产生任何兴趣。
那些机械、呆板的水泥怪物早已“骑”着工业时代四处繁殖,即便在中国,也随处可见。有评论家道:“见到怪物,便‘会隐隐感到忧伤’。”我理解,那是对自己曾经置身其间,或是如今仍在刻板重复的生活的忧伤。只是,在中国,我已经足够忧伤,何必还要跑去德国再来一回。
狂欢灵感从皮肤换到肠胃
飞机拍拍翅膀,离开米兰,仅有54个座椅的小玩具。
我混在一堆正襟危坐的商务人士之间———他们清晨出发,赶到德国打个电话,傍晚再飞回米兰吃饭———我的时间表跟他们如出一辙,心里免不了一番小人得志的窃喜,只不过他们西装领带,我依旧邋里邋遢。
机舱里只装一位空姐,瘦瘦高高,上了年纪,有时笑容可掬,立在过道尽头,有时化作一缕轻烟,钻入扬声器,以山东快书或是黑人说唱且不知句读为何物的速度,播报飞行时间、地面温度、机长又跟老婆吵了一架心情不佳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之类的实用信息。
飞机像一支削去半截的铅笔,掠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上空。我有个朋友,刚刚去过下面,觉得空洞之至,不禁感慨:偌大个世界,还有比瑞士更无聊的所在吗?我望望窗外风景,觉得他言过其实:阿尔卑斯怀抱的座座山峰,高的恰似白色金字塔,低的便是绿色绒布披挂的舞台,与云朵静静相生,蔚为壮观。飞机左侧,一座巨型白色高台;右侧下方,更藏几许幽暗湖泊。
过了阿尔卑斯,便是云海,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作品的画面再次向我脑海中袭来,好似机窗外那阵阵冷风。
我暗自感慨:偌大个世界,还有比杜塞尔多夫更无聊的所在吗?!
米兰赤日炎炎,裸行于市亦觉燥热,杜塞尔多夫却是一番深秋景象。机场外,跌着雨,寒意如刀片。我只穿一件T恤,接我的司机却套上了毛衣。
整个上午,浸泡在郊外的“商务”中,要见的人去了比利时,寻隐者不遇,我昏昏欲睡。到了下午,雨儿收脚,剩下大把时间,只好掷去市区。
面前摆出一桩意外: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,居然并不如摄影学派所描述的那般“忧伤”,倒是淡淡点缀出狂欢———一片区域,时尚店铺密密匝匝,折扣季节登场,无处不是拣了天大便宜似的开怀笑意。
我去了“柯”,一条八十余米宽的大马路,全称柯尼希斯大道。一道护城河,将“柯”一劈为二。河上浮出石桥数座,河边擎起栗树两行。有座石桥,铁制护栏铸满生灵。一只青蛙,栩栩如生,身旁静静荡漾三痕铁波。
另一桥上,恰是俯视河里骑鱼挥叉之海神的好去处。鱼儿口吐喷泉,尾舞如帆。
过河向西,便是旧城,狂欢灵感从皮肤换到肠胃。方圆五百米,处处挨挤餐厅、咖啡店、啤酒馆以至夜总会。一个老头,灌了啤酒,便去一堵墙上挥毫,见我举起相机,他也竖出拇指,墙头那一张张细腻小画,自是他的夜总会。
啤酒花飘香,殒作买醉地
我撞入一堆宏大叙事的石头间,四处瞎转,摸不着头脑,兜个圈子,便忘了哪儿是教堂,哪儿是市政厅,脑子里只印下一处深宅门前的几尺地砖———刻有裸女,刻有怪客,风马牛不相及于豪门背后之庄严宝相。
路过一座瓷器博物馆,一座电影博物馆。后者后庭,藏一片借来的河湾,天光并水色一道阴郁。这画面,适合文德斯,不适合贝歇夫妇。
维姆·文德斯,杜塞尔多夫对当代电影的贡献之一,1945年降生于这座城市。导演之余,文德斯以拍摄照片的方式搜集“真实”世界。他的影像采摘自全球各地,尽管态度冷静,语调节制,却与家乡摄影学派的艺术精神毫无关联,其浓郁的色彩、丰富的奇观,足以引起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的热切回应———我们青睐的隐隐忧伤,依然来自于涂满甜味的天方夜谭,而不是水塔风塔电视塔之类残酷的日常生活。2004年,文德斯颇具《世界知识画报》般大众情怀的摄影展览,在中国一经推出,便成为无数媒体街谈巷议的事件,拨去层层指东打西的迷雾,万花筒玻璃镜片背后深藏的,仍是一桩旧命题: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?
面对这一追问,杜塞尔多夫的另一位儿子,早已给出过自己矛盾的答案。
1844年6月,海因里希·海涅写下《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》一诗,使我这一代中国人,在中学课本里,便认定他是一位以阶级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浪漫主义诗人。
然而,无论于共产主义,还是于浪漫主义,实际上,海涅都是姿态超越的逃跑者。他支持工人阶级,与马克思、恩格斯交好,却从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
他将日常语言诗意化,赋予德语风格的轻松与优雅,但又祭出讽刺性手段,拆解诗意单向度的“浪漫”。海涅擅长创造浪漫,亦懂得跳出浪漫。惟有在亲法并推崇拿破仑这一浪漫事件上,他始终未能超越地逃走。海涅写下《思想·勒格朗集》,倾诉于拿破仑、于大革命之拥戴心情。不知是不是投桃报李,拿破仑居然将海涅的家乡称为“我的小巴黎”。
1797年,海涅诞生于杜塞尔多夫。虽然几百年前,这里只是莱茵河支流杜塞尔河边的一个村庄。但诗人坠地之时,杜塞尔多夫俨然已是一座文化重镇:皇室赞助使得艺术家、作家、音乐家群集于此,1777年甚至成立了艺术学院,时至今日,它仍是德国的重要艺术机构之一。
海涅故居,没于旧城,啤酒花飘香,殒作买醉地。
席卷全球的魔症
走着走着,来到一湾绿水边。德国人说:看哪,这就是莱茵!
河畔立起水泥高柱一根,上端顶出水泥陀螺一只———正是贝歇夫妇青睐的风景。
高柱却非水塔,而是通讯塔,平地拔起两百余米,陀螺中旋转餐厅一家。
海涅的担心,摧毁风景的唯物与激进,早已跳出意识形态樊篱,成为席卷全球的魔症,根系技术崇拜。杜塞尔多夫城里,不乏刻有装饰艺术僵直线条的高大建筑,那便是工业时代发轫之初,人们对于未来的畅想———直线即赞歌,人定胜天,挥别曲线———始于直线的时代,鼎盛于插遍寰宇的水泥高塔。
贝歇夫妇一张一张拍下的寂灭,不是高塔,而是时代的档案。
去河畔不远,一片小广场上,戏谑般立出一根并不高大的粗柱。柱头站的,既非圣徒,亦非陀螺,而是一对身穿彩色T恤的男女。他们手牵着手,莫名其妙眺望远方。
雕塑家想说什么?远方,除了遥远,一无所有。回米兰的天路上,又见云朵中明暗的雪山。
右边一座,如灯笼,包藏闪电,晃动不息。左边一盏,高高挑于远处。
我蜷缩在唯物且激进的机舱里,一边享技术的清福,一边低声诅咒。 |